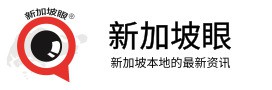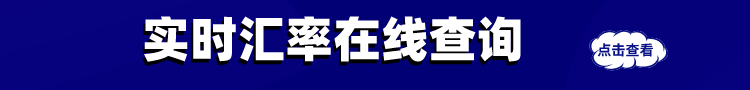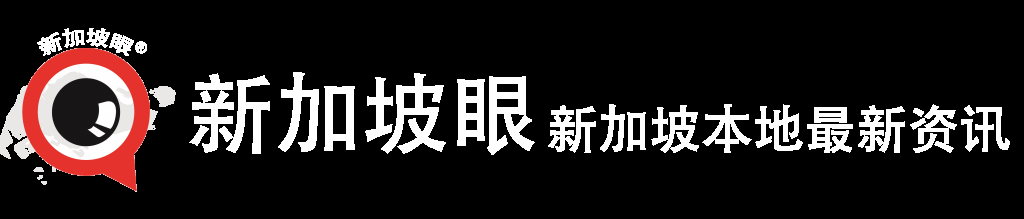| 再过几个星期,就是新加坡国庆了。
(新加坡国庆庆典。图源:国防部) 每到这个时候,我总要想,从19世纪的不毛之地,到开辟成自由港之后的经济腾飞,到3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被迫独立,再到如今的满目繁华。 这一路曲曲折折,磕磕碰碰,但总是绝处逢生,新加坡是怎么走来的? 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穿越回公元1793年,一探究竟。 本文大纲: – 1793年影响新加坡的两件事 – 峇峇娘惹点燃了新加坡的文明之火 – “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英王的华族子民” – 新客的涌入和私会党的兴衰 – 新客点燃了新加坡的文明之火 – 峇峇反思华人文化身份与认同 – 从“英王子民”到“新加坡华人” – 新移民点燃了新加坡的文明之火 – 新加坡为什么成功? 附:来自老徐Sunny的精选点评 1793年影响新加坡的两件事 这一年,是大清乾隆五十八年,老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已经82岁了,三年之后,他将禅位给皇十五子颙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嘉庆帝。 在北京以西8000多公里的伦敦,32岁的英王乔治三世派出以“向乾隆拜寿”为名的使团,抵达北京。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马戛尔尼使团提出了六点请求,包括允许在天津和舟山进行贸易、设立货栈、允许英商自由来往广州和澳门、取消或降低关税、明确订定并公开税额等。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进京面圣) 但清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今尔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把所有请求全部否决。 并且,乾隆告诫英王,如果英船驶至浙江、天津,清朝必定驱逐。 原本通向全球化雏形世界贸易的大门,被无情地关上了。 如果当时中英开通了国际贸易,后世将会怎样发展?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就在马戛尔尼使团进京面圣的同一年,在离北京4000多公里的南边,在华人聚居的古城马六甲,一个男婴出生了。 这个男婴的名字,叫薛佛记。
(马六甲出生的峇峇薛佛记对新加坡起着重要的影响)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进京和薛佛记出世,看似毫无关联的两件事,在短短47年后,竟对新加坡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郑和船队与马六甲 还记得我写过的这篇文章吗? 古代的新加坡王国,由于一顶绿帽引发的丑闻,被满者伯夷灭亡。之后,满者伯夷接着攻打巨港,王子拜里米苏拉带着许多贵族和商人“北狩”,成立了马六甲王国,也就是后来的马六甲苏丹国。 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马六甲苏丹国成了马来半岛最繁荣的海港之一,吸引了不少来自东西方的商人前来经商。郑和七下西洋,就有五次驻节马六甲。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加上福建漳州月港的发展,福建泉漳、广东潮州地区,以及一小部分是广府和客家籍先民,“走线”来到马六甲,并与当地人通婚。他们的后代,男的称“峇峇”,女的称“娘惹”。 由于走线来到马六甲的漳泉人士越来越多,1673 年,郑芳扬和李为经合力建成青云亭,成为明朝走线难民的宗教场所,兼具华人政务、司法作用,也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古庙。
当时马六甲是葡萄牙殖民地。葡萄牙人以“分而治之”的政策管理社会,由世袭的马来君主为马来人的领袖,同时任命华人侨领为甲必丹,即Cina Kapitan,协助处理华侨事务。甲必丹俗称“甲大”,即“甲必丹大人”,亦俗称“甲政”。 根据青云亭资料,马六甲一共有10任甲必丹,郑芳扬为首任,李为经为第二任。在10任甲必丹之后,把甲必丹制度改为“亭主”制度,我们后文会提到这个。
(李为经画像) 早年走线到马六甲的华人,在明朝灭亡之后,他们的后代不认清朝为正统,只认明朝。 例如甲必丹郑芳扬,又名启基。他逝世于1677年,年45岁。明朝早在他12岁时已灭亡,他的甲必丹官职为葡萄牙殖民政府册封,但是,他的神主牌写着的却是“大明甲必丹郑公启基”。
(郑芳扬神主牌) 再例如李为经,他是明朝遗民,1644年躲避兵灾,来到马六甲。他逝世于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但他的画像仍是身著汉服。 郑芳扬、李为经的后代都是峇峇、娘惹。 经过多年经商,有些峇峇成了富商,并且建立起了社会地位和威望。 峇峇娘惹点燃了 说了马六甲,我们把目光转向南边200多公里外的一处岛屿——新加坡。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莱佛士开埠新加坡,并大事拓荒,新加坡成为自由港。 开埠之后五年,1824年,英国人正式从苏丹和天猛公手中买下新加坡,同年,从荷兰人手里取得马六甲管辖权。1826年,把新加坡、马六甲、槟城三地组成“海峡殖民地”,首府设在槟城。 新加坡开埠之后,经济发展势头不错,许多马六甲峇峇富商于是南下发展。 其中一个便是前文提到的,出生于马戛尔尼访华同年的薛佛记。 薛佛记,字文舟,祖籍福建漳州东山。到薛佛记时,薛家在马六甲至少已居住了三代,是地地道道的峇峇。 薛佛记经营矿业,不晚于1826年便南下新加坡。英国人取消甲必丹制度,以“亭主”制度代替。薛佛记的妹夫梁美吉便是青云亭的第一任亭主,而他本身是第二任,由此可知他在马六甲的社会地位。
(图为恒山亭,图源:NAS) 薛佛记到了新加坡之后,不晚于1828年,他仿青云亭体制,在新加坡设立恒山亭,成为闽帮领导机构,因此,史学界把他视为新加坡福建社群的开山鼻祖。 峇峇富商在新加坡开创不少先河:华文学校翠英书院、贫民医院陈笃生医院、市区自来水供应、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南洋孔教会等等。 借用罗振宇在“文明之旅”1012年那一期的比喻——峇峇娘惹融入了新加坡社会的主流,他们带来了文明的火种罐,点燃了新加坡的文明之火。 峇峇成了新加坡的领袖人物 除了福建人的恒山亭,广府人和客家人设立绿野亭以及青山亭,潮州人设立泰山亭,即是坟山和宗教场所,也是最早的社群组织。泰山亭后来成为今天的义安城,恒山亭成了现在的中央医院。福建人设立恒山亭,后来坟场不够用,开始向西边拓展,称为“新冢”,也就是现在的中峇鲁。“中”其实是闽南语“冢”,“峇鲁”是马来语,意思是“新”。
言归正传。1832年,海峡殖民地把首府迁到新加坡,吸引大批马六甲峇峇南下。到了1839年,新加坡闽帮发展得越来越大,事务也愈加复杂。作为义山,恒山亭无法妥善处理社会事务,于是,薛佛记、陈笃生筹建天福宫。同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过了一年,1840年4月,天福宫建成,是福建社群的象征,也是峇峇领导新加坡本地华人社会的象征。6月,英国远征军开抵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在马戛尔尼访华47年后,鸦片战争爆发和天福宫落成,这两件看似毫无关系的事,对新加坡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天福宫落成,标志着以薛佛记等马六甲峇峇富商为代表的“老客”在新加坡生根立足,带来了资金和经商网络;前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开放华工合法出海,一批又一批的“新客”从闽粤琼浙下南洋,带来劳动力和人口增长。 资金、经商网络/劳动力、人口增长,正是新加坡从刚开埠时的小渔村,走到19世纪下半叶朝气蓬勃的港口城市的基础要素。 新客与峇峇 19世纪下半叶大批南下的新客,与19世纪初的峇峇富商,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们只要看看1848年的一个社会统计,从两个侧面就可以看出端倪。 第一个侧面:在峇峇以及闽南、广府、潮州、客家、海南这五大新客社群当中,只有峇峇社群出现了商人阶层,所有新客社群都还没有,顶多就是闽南、潮州、广府社群出现了小店主这一阶层,客家和海南社群甚至连这个阶层都还没出现。经济支配权牢牢垄断在峇峇富商手里。 第二个侧面:娶妻的大概只有2000人,无能力娶妻的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已婚的主要是马六甲峇峇富商,而且是三妻四妾,其次是福建新客小店主。普通劳工、苦力以及没有固定工作的很少有娶妻的。婚配和生育权力牢牢垄断在峇峇富商手里。例如富商章芳琳,就两个夫人、三个女儿、11个儿子。
(人丁兴旺的峇峇家族。图源:NAS) 从这两个侧面,可以说,在19世纪中叶,峇峇和新客虽然共存于新加坡,却是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里,似乎互不交集。 新客苦力大部分希望三四年后就可以回国,但大概只有10-20%做得到,即便回国也很少是衣锦还乡。大部分人五六年,甚至十年才有办法回国,有些十几二十年都回不去,最后客死异乡。 福建有句俗谚:“十去、六亡、三在、一回头”,即说明每十人下南洋,六成客死异乡,三成勉强谋生度日,仅有一成的人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早年的华人苦力。图源:NAS) 那个年代,每年从中国坐帆船到新加坡的新客,大约有1万人;他们有些留了下来,有些分散到马来亚和印尼群岛。每年,从新加坡回中国的大概3000人。来的多,回的少,新加坡人口就这么增长了。 我不是中国人 在新加坡的第一二代峇峇,他们受英文教育,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熟悉英国的规章制度和风俗文化。海峡殖民地政府利用他们对英国和新马本地的知识和人脉,协助治理华人社会。作为回报,在政治上,殖民地政府给予他们崇高的爵位和官职,在经济上,给予他们与本区域其他英国商号做生意的机会。峇峇富商的利益与英国的利益紧紧绑在一起。 1879年,海峡殖民地退休法官J.D.Vaughan写了一本书,谈到了峇峇娘惹这个文化现象。
他在书里写道,海峡华人称为峇峇,与从中国南下的新客区分;他们一方面遵守华人传统,另一方面却鄙视中国华人,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不接受中国华人加入。 在社会上,他们崇尚的是欧洲的娱乐——玩台球、保龄球,喝白兰地和汽水;但是,在家庭里,他们又严格遵守华人传统,尤其是婚嫁、节庆、信仰等民俗。
(1936年宋旺相律师画像,“峇峇三杰”之一) 在政治上,峇峇以英国人身份而自豪。J.D.Vaughan说,如果你当峇峇的面说“你是中国人”,会遭到他们的白眼,并强硬地回应一句“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英王陛下的华族子民(King’s Chinese),有些甚至会加上一句“orang putih”。 “Orang putih”是马来语,“白种人”之意。 刚开始,我看到他们一方面自称“英王陛下的华民”,一方面又严格遵守华人传统礼仪和习俗时,感觉有点儿滑稽——这不是很矛盾吗?
(1889年,新加坡本地峇峇和华人富商向英女王维多利亚敬献雕像) 但是,后来转念又想,似乎也很难怪他们。他们在东南亚出生长大,已有好几代人的时间,生于斯、长于斯;他们有些人去过英国,但从来没到过中国,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个抽象的、模糊的、遥远的概念,跟自己的唯一关联就是祖籍文化和祖宗牌位,而英国则是具体的、清晰的、近在咫尺的利益相关者。 在这种客观情况下,与其指责他们矛盾,我宁可赞扬他们努力保持本身的双面性,至少没有把祖籍文化给丢了。 新客的涌入与私会党的兴衰 中国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厦门小刀会之后,新客大批涌入新加坡,并形成自己的权力中心。 其中一个权力中心便是私会党,包括天地会、洪门、三合会、小刀会等等。而且,不同的新客社群都有自己的私会党,例如,福建帮和潮州帮都有“兴义公司”。
(左右两边有“日”“月”,暗喻反清复明,代表天地会;上下有“青气”“黑气”,代表天和地,也是代表天地会;中间有个“洪”字,用三角形围起来,暗喻三合会) 殖民地政府采取“共存”政策,默许这些私会党的存在,同时,也通过华人甲必丹、峇峇富商和一些新客领袖来“以华治华”。 1854年5月5日,闽潮两帮发生“五斤米暴动”,为期10天,约500死,300间房子被焚毁。峇峇富商和社会领袖陈金声、佘有进出面调停;最后,500人被捕,250人被控,殖民地政府出动30艘帆船,把若干“不受欢迎人士”遣返中国。 到了1870年至1880年间,殖民地政府名册上有将近5万私会党员,超过华人总人口的一半,形成“国中国”。这就难以继续共存了。
(私会党义兴公司总理蔡茂春的墓碑) 于是,1877年,殖民地政府设立华民护卫司,由英国人来处理华人事务,不再委任甲必丹,不再“以华治华”。 在英国人加强华人治理的同时,清朝也认识到治理海外华侨的重要性。同一年(1877年),清朝任命胡亚基为领事;1881年,31岁的左秉隆接任为领事,是清朝第一个派驻新加坡的职业外交官。 清朝委任驻新加坡领事,在历史上是件大事。前文已述,峇峇对中国的概念是抽象的、遥远的,自己跟中国的关系局限在小小的家乡里;但是,清朝派驻领事之后,大大拉近了心理距离,对峇峇来说,中国现在是具体的、可以触及的,自己跟中国的关系远远不止小小的家乡,而是放眼整个中国。 新客点燃了新加坡的文明之火 19世纪下半叶大批新客涌入,假以时日,出现了一个必然结果。 那就是新客富商和精英的出现,例如厦门集美的陈嘉庚、同属厦门的林推迁、福建金门的黄庆昌,也就是大华银行黄祖耀的父亲。 这一批新客富商和精英,接过了峇峇富商的棒子,创办了中华总商会、华侨中学等重要机构,尤其在三四十年代,主导了南洋华侨的大部分事务,包括支援中国抗日,可以说,新客点燃了新加坡的第二场文明之火。 与其同时,峇峇开始反思华人身份与认同,而且更加积极参与到跟中国有关的事务。我举两个例子。
峇峇林文庆,是东南亚拿女王奖学金(今天的总统奖学金)到英国留学的第一人。在留学时,他华语不行,中国留学生不认他为华人,他于是发奋学习中文。后来,他在新加坡设立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SCGS、中正中学、华文的书报社、开设华语学习班,放弃基督教,改信孔教,并创办南洋孔教会。
另一个例子是峇峇林义顺和他的舅舅峇峇张永福。他们追随孙中山,创办同盟会南洋分会;张永福把晚晴园交给孙中山住,孙中山在那里策划了三次起义。辛亥革命的成功,与新加坡峇峇和华侨有密切的关系。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峇峇盛极而衰。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新客富商的崛起和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挤压了峇峇富商的致富空间。 更为关键的是,日本南侵,英军战败投降。一朝天子一朝臣,百多年来与峇峇休戚与共的英国不再掌权,峇峇富商熟悉的世界秩序土崩瓦解。峇峇领袖林文庆甚至被迫领导华社向日寇献上5000万元奉纳金。
(”华侨协会“会长林文庆被迫领导华社向日寇献上5000万元奉纳金) 1945年,日寇投降。英国重返新加坡。但是,峇峇富商当年的辉煌与荣耀已不复来。 有意思的是,在新加坡的权力中心,取而代之的,却是另一批峇峇。 但他们不是峇峇富商,而是峇峇知识分子。 你知道吗?新加坡自治邦内阁的九人当中,就有四个峇峇——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林金山;其他五人有两个华人、一个马来人、一个印度人、一个是欧亚混血。 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林金山不是峇峇富商,而是峇峇知识分子。士农工商,“士”的地位终于又升到了Number One.
从“英王的华人”到“新加坡华人” 这张照片里的小男孩是谁?
没错。他就是4岁的李光耀小弟弟,就出生在峇峇家庭。 然而,现在你如果跟人说李光耀是峇峇、李显龙是峇峇,肯定被嗤之以鼻。 道理很简单,到了本时期,峇峇已经融入了新加坡华社,不再具有当年独特的峇峇娘惹文化特性了。 他们已经完成了从“英王陛下的华族子民”到“新加坡华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转变,与你我别无二致。 新移民 到了2025年,新加坡独立就要60年了。 这60年来,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毫无疑问具有本土意识和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陆陆续续来到本地的新移民,有些已经充分融入,有些还在融入中,有些可能不容易融入,但是,到了“移二代”,融入应该很丝滑。 无论是否已经融入,一个无可否认的是,新移民也给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文明的火种罐,无论在工商界、学界、文化界,新移民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也带来了可贵的启发。 正与当年峇峇、当年新客一样,新移民已点燃了新加坡新一代的文明之火。 新加坡为什么成功 新加坡为什么成功? 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海纳百川,张开双臂欢迎四方移民,就如李斯所说“地无四方,民无异国”。 一代代的移民造就了今日繁华的新加坡,而新加坡也成就了一代代的移民。 从峇峇娘惹到新客,从新客到新一代的中国新移民,他们来自马六甲,来自闽粤琼浙,来自中国的五湖四海,最终融入了新加坡社会;他们带来了文明的火种,点燃了新加坡的文明之火,不断注入文明的养料。 与其同时,对于新客和新移民的祖国,新加坡也回予善意——辛亥革命、南侨机工、中国改革开放、苏州工业园区……
(6月22日,在“得到 新商学”第四期“一起看文明”活动上,作者做了“消失在历史长河的先驱华人——峇峇娘惹”为题的讲座。本文是该次讲座内容的节选) 附:精选点评 当年的“峇峇娘惹”坚守中华传统习俗,却只承认是英国”king’sChinese”,如今族群还在,这个历史长河里短暂的文化却因为新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而逐渐消弭。 窃以为,这个文化现象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海外华人宗族的血统认同和政治的宗主国归属感产生分离而产生的。 宗族的血统认同,无论方言异同,华人文化一脉相承,从未改变,对于政治身份归属却与宗主国的政权更迭、国力强弱息息相关。 所以,第一批明末为避清祸而来的移民,即使在清朝已经建立多年,仍然着汉装,传汉习,对于古国的印象和概念,从最早的反清复明,到后来停留在遥远的“乡下家乡”,因而在政治上更偏向于能直接得到的英王恩庇,而殆于承认与东方古国的隶属关系。 待到清朝在南洋设立领事制度,和又一批新移民在南洋的崛起,东方古国的影响力又勾起峇峇们基因里华人寻根情节,老客们甚至开始回到清朝为家族捐官立万,直到民国“南洋三杰”回国任职、陈嘉庚等杰出华人深度参与古国的现代政治生活。 这些海外华人社群发展,无不从另外一个平行世界折射东方古国的每一个历史进程。故土不离,是写在华人骨血里的基因,离乡别土,各个时期都有各个时期的原因。凡百年前,下南洋,讨生活的,大都来自是自然资源匮乏的粤闽蛮荒之地,江浙自古富庶,所以海外有历史的江浙会馆寥若星辰,最近几十年却逐渐壮大。 许博士的讲座最后说,华人移民如火种在东南亚遍地开花,也为东南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新客老客经年的努力和奋斗造就了如今的新加坡,新一代移民会给南洋和华人带来怎样的变化,他在文稿里打了个问号…… 同日,同城,吴晓波与秦朔这两个复旦新闻系同班的财经文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盛大的“出海”论坛,是否已经给出了答案? 是夜,新加坡国庆预演,滨海湾烟火璀璨。
ABC丨编辑 KS丨编审 免责声明: 1.凡本网站注明文章类型为“原创”的所有作品,版权属于看南洋和新加坡眼所有。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时必须注明:“文章来源:新加坡眼”。 2.凡本网站注明文章类型为“转载”、“编译”的所有作品,均转载或编译自其他媒体,目的在于传递更多有价值资讯,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相关阅读 |